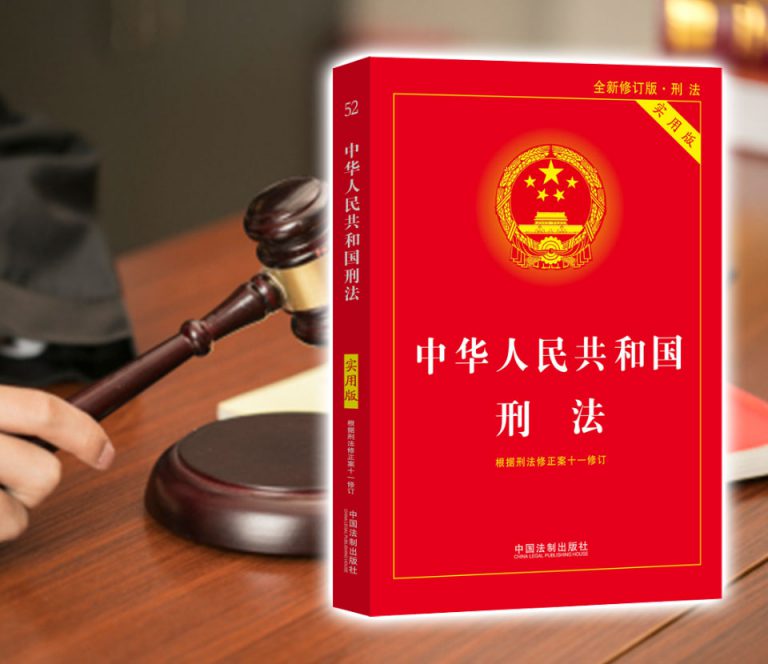
近10年來,國民對祖國「司法部門」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所做出的艱苦努力沒有太多關注。更令人非常遺憾的是,特區絕大多數媒體機構未能對現代《中國刑法》發展與完善新聞報道層面立下寸功。筆者選文,圍繞2016年「劉吉強凶殺上訴案」(「劉案」)進行討論,旨在向民間發出相關訊息:我國全體國民應對《中國刑法》發展與完善工作有整體的認知與心存積極態度。筆者重點介紹我國「司法部門」為實現更好的「中國式正當司法」(Chinese Sty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所採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

「劉案」不僅給劉先生本身帶來過嚴重的不公平遭遇,也同時反映出我國刑事訴訟程式理論與實踐曾經的巨大距離。劉先生曾三次被法院判定故意殺人罪,判處死緩。在進行第四次上訴前已蹲了18年的大獄。2016年,本文筆者之一代理辯護,上訴「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重審「劉案」。案終,原判決被推翻,劉先生重獲自由,無罪當庭釋放。

由於任何一項關於評估證據可採性的立法在頒布後能否成功付諸實施具不確定性。因此,原審法官在根據相關立法原意解釋該法時發揮著不可或缺的法律實踐作用。但在「劉案」中,物證的歸納與評估存疑。劉先生在法庭偵訊後被定罪,部分定罪基礎是他的「非自願認罪供詞」(Involuntary Confession)[違反1996年《中國刑事訴訟法》(《刑訟法》)第43條,參見:2018年「刑訟法」第56條];其他部分定罪基礎針對極富爭議性的相關薄弱「環境證供」定罪比重(Circumstantial Evidence)。
那天是1998年2月14日。年輕的劉先生被指控殺死他18歲的女友,所以他也被冠上「情人節命案殺手」這個稱號。但是,證據鏈(Chain of Evidence )沒有目擊證人與關於所指控罪行為的有力「環境證供」支持,從中推斷出有爭議的事實。劉先生最初是承認殺人,但根據他的辯護大律:他的「認罪供詞」是有人通過酷刑與非法訊問獲得的(註1)。
1996年《刑訟法》第四十三條(註2)規定必須按照法定程式收集證據,並規定:「… 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換言之,人民法院既要處理相關「認罪供詞」入罪部分的不利影響(Prejudicial Effect of Inculpatory Statements),同時也要處理相關「認罪供詞」脫罪部分的論證價值(Probative Value of Exculpatory Statements)。混合「認罪供詞」(Mixed Statements)的提取自願性原則必須遵守(Voluntariness of Confession)。
第46條規定(註3):「…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另一方面:「… 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根據特區著名法律學者陳弘毅教授的著作《中國法概論》,陳老師認為,《刑訟法》 1996年版沒有提供詳細人民法院提取證據的規則(註4)。
原審法官是合理與專業事實調查員,不應對劉先生對「非自願供詞」所提出壓倒性證據視而不見。偵訊後不久,劉先生被帶入監獄,數名與劉先生同監捨關押人員與監管民警證實他入監時身體有傷。此凶殺案主控審判必敗的重點是1998年2月22日14時10分至16時35分,偵查機關與吉林市船營區人民檢察院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對劉吉強訊問,形成二份內容相似的有罪供述訊問筆錄(註5)。
在本案中,除了劉先生的認罪外,沒有其他證據證明他在犯罪現場或周邊地區曾經出現並實施犯罪行為。此外,「環境證供」薄弱。「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原判、改判劉吉強無罪。劉先生於2016年4月被釋放。本文筆者之一蔡大律在法官席前陳詞道:「[劉先生]的招供都是偵訊人員通過刑訊逼供提取的非法陳述(註6)。
在「普通法」制度下,「案中案」(Latin: Voir Dire)用於審查被告所作的招供是否應被法庭接受(Admissibility of Confession)。在特區謀殺案審判中,高等法院原訟庭大法官必須屏退陪審團,單一負責聽取大律師關於是否應該接受此項證據的法律陳訶。相關法律程序作用在於避免陪審團聽取可能隨後被法庭頒令不可呈堂的「認罪供詞」,慎防陪審團聽取後可能形成的偏見的風險(註7)。
在律政司司長 訴 林達明一案中(註8),特區終審法院清楚指出:「19. 控方必須證明有關的陳述是自願的陳述,意即該陳述並非有權力的人因激起被告人恐懼其權益受損或令被告人抱有得享利益的希望或藉壓迫手段而從被告人處獲取。…」。此外,「普通法」賦予大法官「司法剩餘酌情權」(Residual Discretionary Power),可在特定情況下頒令某些「認罪供詞」不可呈堂,以確保被告得到公平審判(註9)。

針對《刑訟法》 1996年版沒有提供詳細人民法院提取證據的規則,我國「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發佈了若干「民事與行政訴訟證據細則」的司法解釋檔,未來刑事證據規則很可能也會通過「司法解釋」形式引入《中國刑法》(註10)。為了順應我國的法律改革思潮,《刑訟法》 2018年版中的證據規則比它的1996年版在基礎上有更加全面的規定。
還值得注意,「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實施細則(《實施細則》),初步確立法律制度的判例制度(Law of Precedent)。《實施細則》第七條明確規定:「案例指導辦公室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研究的備選指導性案例,可以徵求相關國家機關、部門、社會組織以及案例指導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專家學者的意見。」(註11)。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應參考「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指導性案例(註12)。
作為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劉先生被無罪釋放向外界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即:祖國司法機構將不再容忍司法不公。祖國刑事司法系統中的可能程式缺陷(Procedural Defects)也不會再被允許生存在內地法官們的眼皮底下。同樣值得關注,「劉案」是吉林省首例在「中央政法委」發佈《有效防止冤假錯案條例》後,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定罪的首案(註13)。
註 1: 法廣「三判死緩 「情人節兇手」入獄18年後獲無罪釋放」30.04.2016 available at:
https://amp.rfi.fr/cn/中國/20160430-三判死緩-「情人節兇手」入獄18年後獲無罪釋放
For English news coverage, see: The Nation「China’s Valentine’s Day killer acquitted of 1998 murder」01.05.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nation.com.pk/01-May-2016/china-s-valentine-s-day-killer-acquitted-of-1998-murder
註 2: 維基文庫「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1996年)」available at: 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_(1996年)
註 3: 同前
註 4: Albert Ch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ong Kong LexisNexis 2004 at p 213
註 5: 同上,註 1
註 6: 同前
註 7: Mike McConville & Dmitri Hubbard「Hong Kong Law of Evidence」Hong Kong: Blue Dragon Asia Ltd. 2014 at p 29
註 8: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am Tat Ming (2000) 3 HKCFAR 168 at §, available at: https://www.hklii.hk/chi/hk/cases/hkcfa/2000/90.html
註 9: Simon Young「Hong Kong Evidence Casebook」Hong Kong Sweet & Maxwell 2004 at p 551
註 10: 同上,註 4
註 11: 上海投資網《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實施細則 available at: http://www1.shanghaiinvest.com/cn/viewfile.php?id=9500
註 12: Hu Zhenyuan, 「CGCP Interview: Dr. Hu Zhenyuan」in China Law Connect Issue 1 June 2018 at p 69;
Also see: 斯坦福大學CGCP Classroom特輯 available at: https://www.sohu.com/a/240668289_740368
註 13: 同前

文:蔡可尚
《中國夢智庫》中國刑法訴訟與實務高級顧問
北京青葵律師事務所創辦人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北京師範大學刑法學博士後
文:丁煌
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經民聯港島東支部主席,「中國夢智庫」主席
城市智庫成員,刑事辯護大律師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顧問委員會成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中國夢智庫》是一間扎根特區的非牟利團體;與心存熱誠的資深義工、專家與職業專業人士們合作,攜手「說好中國故事」。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