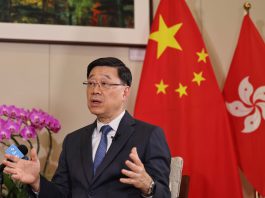之前的文章提到近期正在進行刑期覆核上訴的「呂世瑜案」,源於原訟庭以本地法院在「吳文南案」中提出的量刑指引,原想給予對方認罪扣減,但又裁定對方案件屬「情節嚴重」,而「情節嚴重」在《港區國安法》中訂明了法定最低刑為五年有期徒刑,才會衍生所謂宣告刑能否低於法定最低最低刑的爭議。可是原訟庭的裁決本來便有問題,因為認罪從來不是《港區國安法》第33條的法定減刑情節。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港區國安法》第33(二)條列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從輕、減輕處罰,但在法院的審訊程序中,被告人在審期未定前認罪,法院便不會考慮控方證據的強弱,被告人根本不須在法院「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除此之外,第33(二)條在「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之前,尚有「自動投案」之條件,兩句中間用的是「,」,意味着這一條款的真正意思,是指被告人自首並向警方主動交代自己的犯罪情節,而非在庭審前認罪。
如此一來,由於《港區國安法》的法律位階高於本地案例法,被告人除非有法定減刑情節,否則法院不應予以減刑,可見原訟庭在「呂世瑜案」的裁決,乃是將本地案例法「僭建」於《港區國安法》第33條之上。更重要的是,由於現時「呂世瑜案」的刑期上訴,乃是由辯方提出,爭議點在法院宣告刑能否低於法定最低刑,律政司並沒質疑本地案例法中的認罪扣減原則,究竟是否適用於國安法被告人,根據普通法的遵從先例原則,未來法官在量刑時,便可根據「呂世瑜案」此一案例,給予被告人認罪扣減。
上月底審結的「賢學思政案」,便是典型例子。被告人三人判囚30至36個月,表面上看來刑期不輕,但是法院為免受呂世瑜的上訴案影響,陷入宣告刑能否低於法定最低刑的爭議,索性指案件屬「情節較輕但偏近嚴重一端」,將王逸戰的量刑起點,分別定為4年9個月,再以王逸戰犯案時未滿21歲、審期未定前認罪,減刑3個月後再扣減三分一刑期。被告人陳枳森和朱慧盈亦獲三分一認罪扣減,黃沅琳則被判入教導所。
縱觀「賢學思政案」,法院除了把「呂世瑜案」為被告人可獲認罪扣減的案例外,其實還有另外兩個問題:首先,控方曾質疑王逸戰在求情階段發表的公開信,顯示被告沒悔意,但法官根據「馬俊文案」,指被告有否悔意,不構成加刑或使案件變嚴重的因素。換言之,法院在被告人沒國安法法定減刑情節的情況下,除了引用本地案例給予認罪扣減外,又引用另一個本地案例,加入認罪有否悔意不會影響減刑的元素。
第二個問題是以被告人作案時的年齡,作為減刑或不判監禁的理據。法院判黃沅琳入教導所,主要是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9A 條規定:「對任何年屆16歲或超過16歲而未屆21歲的人,法庭除非認為沒有其他適當的方法可處置該人,否則不得判處監禁」,但這是本地法例,《港區國安法》第33條沒有判刑時年齡未滿21歲,可獲從輕處罰的規定。
另一方面,《港區國安法》訂明的處罰方式,只有「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於香港沒有「拘役」和「管制」的處罰方式,所以法官能判的處罰,理應只有香港慣稱為監禁的「有期徒刑」,現在判黃沅琳入教導所,其法理依據如是建基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9A 條,無疑是變相把本地法例和案例凌駕於《港區國安法》之上的另一案例。

退一步而言,即使假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9A 條適用於國安法案件,條文中的「超過16歲而未屆21歲」,亦應當是指判刑當日未滿21歲,王逸戰在判刑之日已經超過21歲,法院又憑什麼以案發時對方未滿21歲,作為減刑3個月的理由?似乎,法院是根據終審庭於 2018 年「梁曉暘案」的判詞中指,法庭判刑時對於年齡的計算毋須過於執着,所以把案發日年齡亦視為減刑理由,而這做法其實等於把另一本地案例「僭建」在《港區國安法》第33條之上。
由是觀之,香港法院正在引用多項本地法例和案例,為《港區國安法》「僭建」多項減刑條件。至於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問題,上訴庭判詞強調要採用所謂的「國際間的司法標準」,更讓人擔心法院想透過引用外國法例或案例,乃至是透過越權行使所謂的「違憲審查權」,藉此「閹割」《港區國安法》,只是為了方便大家閱讀,此一問題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